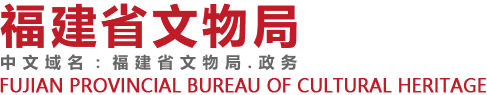一张摄于1931年的老照片悄然面世,揭开了一座早已消失在漳州一中芝山校区的“裕康楼”神秘面纱。这座楼的名字,承载着一位鞠躬尽瘁的教育先驱的故事,也串联起漳州与诏安两地、跨越近百年的守望与纪念。且看——
前不久,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迎来了建校120周年的盛大纪念。这座拥有双甲子历史的学府,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而一张摄于1931年的老照片,恰似一把钥匙,轻轻开启了那扇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让一段关于建筑、人物与教育初心的珍贵往事,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这张照片现存于漳州一中红色文化博物馆。据漳州市政协文史员、该馆馆长林宪杉介绍,照片中所摄的,是早已拆除的芝山校区五爱楼的前身——“裕康楼”。尽管建筑本身已不复存在,但这张照片却无声地讲述着一位教育先驱在此鞠躬尽瘁的往事。
一张照片,揭开尘封校史
“要了解裕康楼,必先了解沈裕康。”林宪杉翻开那泛黄的史料,仿佛打开了时光的宝盒。1929年,福建教育界迎来重大变革,省立第八初级中学和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分别更名为省立龙溪初级中学(漳州一中前身)和高级中学(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前身)。次年8月,34岁的沈裕康从诏安县教育局局长一职,被省里调任为省立龙溪高级中学校长。
在林宪杉看来,这位从诏安走出的教育家,人生轨迹堪称传奇。
1895年,沈裕康出生于诏安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在族人资助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赴日本、东南亚考察教育。学成归国后,他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任训育主任,1926年回到诏安县任县政府教育科长、诏安县教育局局长。
“他在诏安推行教育改革,实行教师公开考试,按等级定薪,选拔优秀教师任校长,使当地教育面貌焕然一新。”林宪杉指着史料上的记载说。这些改革经验,为他后来在漳州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0年的漳州,教育界正热议学校发展大计。芝山因环境优美,又是朱熹读书处,被公认为理想办学地点。沈裕康到任后,与时任漳州驻军师长多次商议,最终促成两校合并。
1930年10月,省教育厅正式发文,两校合并为福建省立龙溪中学。“这是漳州一中和漳州城市职业学院两校前身的重要历史交集。”林宪杉说。
一个名字,铭记一位校长
据档案记载,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新校舍于1930年底动工,由漳厦大新建筑公司承建。建筑费白银4.6万元。
“裕康楼是座中西合璧的三层建筑,”看着已经发白的老照片,林宪杉饶有兴致地将裕康楼原有的风貌娓娓道来,“红砖清水墙,百叶窗,宽40余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最特别的是中间四根水泥柱形成的三角形立面,在当时颇具特色。”
1931年夏,新校舍如期竣工。其中一座集教学、礼堂、图书馆功能的二层大楼取名“干之樓”(今新华楼);另一座教学与宿舍等多功能的三层建筑,为纪念为建校呕心沥血的沈老校长,被命名为“裕康楼”。
令人惋惜的是,沈裕康未能亲眼见证学校的蓬勃发展。学校筹建期间,事务繁杂。沈裕康因苦心经营,日夜奔忙于两校合并及筹建校舍事宜,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病,终因医治无效,不幸于1931年11月间与世长辞,年仅36岁。
这座纪念建筑的命运也随时代变迁而波折。新中国成立后,因提倡“五爱”道德规范,裕康楼更名为五爱楼。历经数十年风雨,建筑出现老化漏水,最终在2004年因扩建图书馆的需要被拆除。
“建于裕康楼(五爱楼)原址的芝山校区图书馆如今已成为校园文化阵地。相比同期建造、至今犹存的新华楼,裕康楼的故事渐渐被遗忘。”林宪杉不无遗憾地说。
一座小楼,见证一门风骨
沈裕康生前廉洁自律,逝世后未留下多少家产,家中仅留下32岁的妻子和五个年幼子女,生活困顿。学校师生和漳州社会各界感其事迹,集资援助遗属。部分款项用于在诏安故居旁购置一处老屋,拆除后新建一栋两层小楼供家人居住;余款存入钱庄,利息补贴家用。
“这座仅50多平方米的小楼,曾是全家人的庇护所。”据沈裕康的后人沈少箴介绍,这座曾居住着沈家三代人的祖屋,因紧邻明代“天宠重褒”牌坊,于2017年配合文物保护拆除了一大半建筑。
2024年,沈家后人对剩余部分进行了修缮。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李木教闻讯有感,特意题写“裕康楼”三字,镌刻于二楼门匾。
“如今在诏安,也有一座裕康楼。”想起儿时在祖屋生活的点点滴滴,沈裕康的后人不禁感慨,“虽然芝山的裕康楼已不复存在,但这座小楼将永远铭记祖父的教育精神。”
从漳州芝山到诏安古城,两座裕康楼见证了一位教育工作者鞠躬尽瘁的一生。这段跨越近百年的教育回响,在漳州城市职业学院120周年校庆之际,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追寻裕康楼的故事,不仅是追溯一段校史,更是对教育初心的回归与致敬。”望着这张老照片,林宪杉表示,它不仅是一座建筑的记忆,更是一种教育精神的传承与延续。
(漳州融媒记者 许文彬)
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
-
重点网站
-
全国各省区市文物部门网站
-
全省文博单位
-
其他链接